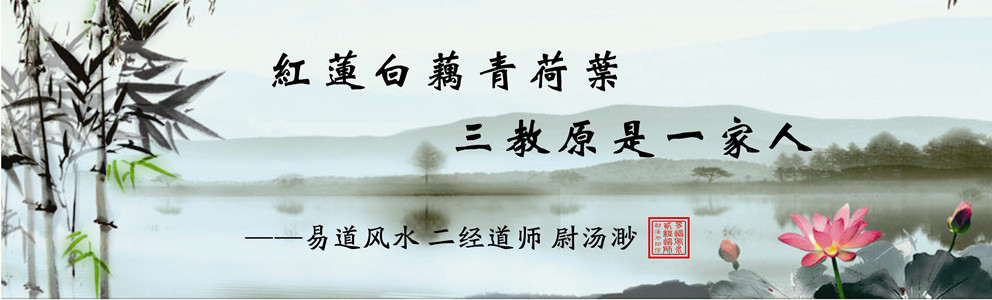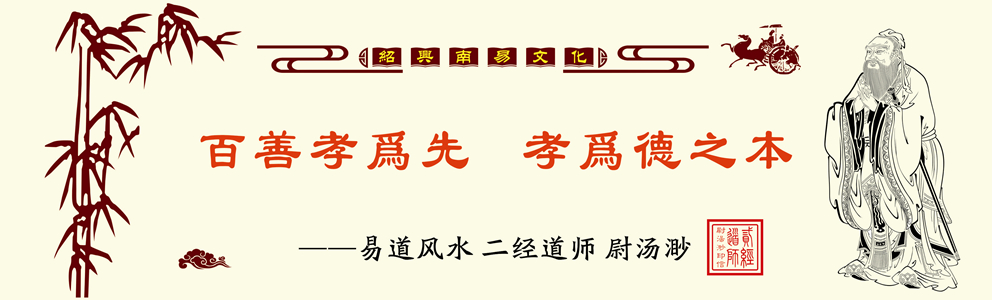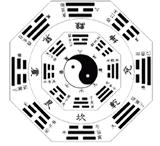圣人孔子与易经
易道风水文苑
孔子与《易传》—论儒家形上学体系的建立
按太史公的说法,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,序《彖》、《系》、《象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”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,本文述孔子言行多以此为据),十分明确地认为,孔子是《易传》的作者。太史公从杨何受《易》,所述必有来历。然而,自北宋欧阳修作《易童子问》以来,这一说法受到了怀疑。数百年来,置疑的范围不断扩大:从开始怀疑部分《易传》非孔子所作,直到认为整个《十翼》皆非孔子作品。20世纪上半叶,《十翼》非孔子作品已成了多数人的共识。然而,这一所谓“定论”,随着帛书《易传》及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,而被彻底推翻了。《史记》所载不诬,《易传》为孔子晚年所作,这应是今天学术界的共识。这是本文立论的基础。
一、 孔子作《易传》的目的
《易经》是周代上流社会的常见典籍,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占卜吉凶。这一点我们从《左传》17处对《易经》的引用上,可以明确地认识到。孔子对《易经》的认识,与时人相比,既有相同之处,也有不同之处。相同的是利用《易经》的占卜功能,预卜行为的吉凶结果。因为我们看到孔子也曾经多次运用《周易》占卜,并且,从没否定过《周易》的占卜功能。不同的,也是凌越时人之处是,孔子并没有停留在《易经》的卜筮功能上,而是更多地关注其道德因素。此义帛书《要》篇记载的十分清楚:子曰:易,我后其祝卜矣,我观其德义耳也。后世之士疑丘者,或以易乎?吾求其德而已,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。君子德行焉求福,故祭祀而寡也;仁义焉求吉,故卜筮而希也。祝巫卜筮其后乎? 通过上述,我们看到孔子对《易经》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其“古之遗言”上,关注的是其道德训诫意义。但是,需要指出的是,仅停留在道德层面的人伦意义来评价《易传》却是不恰当的。孔子作《易传》别开生面,并非是为了作《易传》而作《易传》,这与汉学家标榜的严守经文的疏释原则是绝不相类的。这一特点,前人早已注意到了,《朱子语类》说:伏羲自是伏羲《易》,文王自是文王《易》,孔子自是孔子《易》。伏羲分卦,乾南坤北,文王卦又不同。故周易“元亨利贞”,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于正,孔子方解作四德。(《朱子语类》卷第六十七)
意识到《易经》历经三圣,面目各异,是朱子的犀利之处。然而,朱子认为“元亨利贞”至“孔子方解作四德”,是不确切的。《左传》襄公九年载:
(穆姜)始往而筮之,遇艮之八,史曰:“是谓艮之随。君必速出!”姜曰:“亡。是于《周易》曰:随,元,亨,利,贞,无咎。元,体之长也;亨,嘉之会也;利,义之和也;贞,事之干也。有四德者;随而无咎。我皆无之,岂随也哉?必死于此,弗得出矣。”
这说明,早在孔子之前就有用“四德”来解释“元亨利贞”的传统了(对文中所引《周易》与孔子《易传》的关系,章太炎谓:“今思之,或文王以后,孔子以前说《易》者发为是言,而孔子采之耳。”(《国学讲演录》69页)《左传》杨伯峻注谓:“此八语皆见《易·乾·文言》,惟两字有不同。穆姜非引《文言》,乃《文言》作者袭用穆姜语。” 文中明言,穆姜与人言征引《周易》,则此一《周易》绝非穆姜一人所独见,章说谓孔子作《易传》前就有解《易经》的文献,孔子《易传》有采撷旧文之处,实为近理之言,杨说则显然难从。)。以道德的角度阐扬易理,不是孔子的发明,孔子作《易传》的真正价值并不在此。谈到孔子作《易传》的价值,章太炎认为:
孔子赞《易》之前,人皆以《易》为卜筮之书。卜筮之书,后多有之,如东方朔《灵棋经》之类是。古人之视《周易》,亦如后人之视《灵棋经》耳。赞《易》之后,《易》之范围益大,而价值亦高。《系辞》曰:“夫《易》何为者也?夫《易》开物成务,冒天下之大道,如斯而已者也。”孔子之言如此。盖发展社会,创造事业,俱为《易》义所包矣。此孔子之独识也。
章氏是一代国学大师,所论自有其不可磨灭之处,但若从孔学的整体来看,当能发现孔子作《易传》有更深层的涵义。我们知道,孔子一生力倡仁政,强调“反躬修己” 、“克己复礼”,从人的内心出发,启发人的道德自觉,体现了强烈的人本理性精神。这类例子在《论语》中比比皆是,兹不赘举。值得注意的是,孔子的这种诉诸内心直觉的道德证明方式,常常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。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《论语·阳货》篇的宰我问孝:宰我问:“三年之丧,期已久矣。君子三年不为礼,礼必坏;三年不为乐,乐必崩。旧谷既没,新谷既升,钻燧改火,期可已矣。”子曰:“食夫稻,衣夫锦,于女安乎?”曰:“安”。“女安则为之!夫君子之居丧,食旨不甘,闻乐不乐,居处不安,故不为也。今女安,则为之!”宰我出。子曰:“予之不仁也!子生三年,然后免于父母之怀。夫三年之丧,天下之通丧也,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?”
这里暴露的问题是:仅仅从良知上论证道德的正当性,并不能保证论证的效果。事实上,同样从良知出发,人们的道德抉择往往是很不相同的。人们是否拥有共同的良知,是大成问题的。这就迫切需要为道德的存在寻找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依据。孔子素来以仁义自任,却一生坎坷:干七十二君,十四年去国流亡,频遭排挤、冷遇,危难之际,连长期追随他的及门弟子也产生了疑惑和动摇。道德信仰迫切需要在更高的范畴上得到证明,能够满足这一需要的只有“弥纶天地”的易道。孔子作《易传》,为道德的合理性提供了最终的形上学依据,并因之确立了深邃、严密的贯通人天的“性命”(尽性至命)修养学说。这固然与易道“与天地准”的本身特点有关,但是,“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”,孔子对形上境界超凡的领悟力,邃密笃实的性命修养,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。
二、《易传》中的道德形上学体系
(一)道德存在的形上学依据
孔子一生关注伦理道德,这一点,古今学术界少有异辞。值得注意的是,尽管《易传》中充满了类似“君子以……”的道德训诫,《易传》的真正用意却不在重复这些“古之遗言”,而是为道德确立坚实的形上学基础。对此,“广大悉备”的易道似乎给出了天然的答案:
天尊地卑,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陈,贵贱位矣。动静有常,刚柔断矣。方以类聚,物以群分,吉凶生矣。在天成象,在地成形,变化见矣。是故刚柔相摩,八卦相荡,鼓之以雷霆,润之以风雨,日月运行,一寒一暑。乾道成男,坤道成女。乾知大始,坤作成物。乾以易知,坤以简能。易则易知,简则易从。易知则有亲,易从则有功。有亲则可久,有功则可大。可久则贤人之德,可大则贤人之业。(《系辞上》)
可以看出,在“刚柔相摩”、“动静有常”的易道演化之中,人类的道德现象(贤人之德)只是其中合乎规律的一个环节,是顺应乾坤之道的当然呈现现。《易传》又谓:为书也,广大悉备。有天道焉,有地道焉,兼三才而两之,故六。
可见,道德作为人道中事,本身就是易道的一部分,它存在的正当性的依据不在其自身,而在于更高层次的天地之道——易道。“生生之谓易”,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,作为易道演化的表现,从本质上说,道德的动力来源于天地大德——生生处息的功能。
这一认识也表现在《序卦传》对六十四卦排列顺序的哲理化解释上。《周易》中的吉凶卦象均是作为易道演化的结果自然地生成出来的。吉类的如:“履而泰然后安,故受之以《泰》”、“有大而能谦必豫,故受之以《豫》”、“物不可以终止,故受之以《渐》”。凶类的如:“进必有所伤,故受之以《明夷》”、“家道穷必乖,故受之以《睽》”、“物不可以终通,故受之以《否》”。报有吉凶都是易道演化的一环,都是易疲乏规律的表现,这一点,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“是故天生神物,圣人则之,天地变化,圣人效之。天垂象,见吉凶,圣人象之。河出图,洛出书,圣人则之。”即使是圣人,在易疲乏面前,也只能是“则之”、“效之”、“象之”,这也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根本原因。反之,如果是圣人立道,天地则之,则显然荒谬,不能成立。这正充分说明了人的局限性,人并不拥有道德的最终立法权,这个权力只能不自超越人类的易道,来自其表现出的和生不息的功能。
《易传》还证明道德具有永恒的特点,它永不消失,万古长存。这自然也是易道的特点决定的:乾坤其易之蕴邪?乾坤成列,而易立乎其中矣。乾坤毁,则无以见易,易不可见,则乾坤或几乎息矣。(《系辞上》)
意思是,易道作为大道,天地万物是它的表现形式。如果天地万物不存在了,也就无从认识易道了。反之,如果易道不存在,那就只有一种情况——乾坤运行停止,万物消失。正反两方面说的是同一个意思,即强调易疲乏与天地共在的永恒性。于是,合乎逻辑的认识就是,体现了易疲乏的人类道德也与易疲乏一样,与天地共存,永恒不灭,万古如斯。这样,道德就成了绝对的律令,人类只能严格属守,它的至高无上性和永恒性都是不容置疑的。需要指出的是,孔子将人类道德的存在依据归结于形而上的易道,丝毫没有损害人性的高贵、削弱人的道义自信。相反,为矢志投身于“仁义”之域的儒者,提供了无限的道德勇气和绝对的自信。因为,他们的道德实践体现的乃是宇宙间最高的真理。惟如此,他们的生命才获得了莫大的价值,才是尊贵和伟大的。
(二)尽性至命——对道德功利论的超越
《易经》作为卜筮之书,它的主要功能就是预卜事物的吉凶悔吝。如果我们细玩经文,就会发现,经文中表现的价值观相当中立,基本上没有从道德标准来看待吉凶。否则,就不会有《观》之初六的“童观,小人无咎,君了吝”,《否》之六二的“包承,小人吉,大人否亨”,《大壮》之九三的“小人用壮,君子用罔”。以道德根源来解释《周易》占卜结果,应当是周代礼乐文明大兴之后的事。除上文所引的《左传》襄公九年穆姜的话以外,还有昭公十四年的记载:
曰黄裳,元吉。以为大吉也。示子服惠伯,曰即欲有事,何如?惠伯曰:“吉尝学此矣。忠信之事则可,不然必败。且夫《易》不可以占险。”
充分说明,以道德定吉凶已成了当时的共识。周人的这一认识传统在孔子的《易传》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继承。但严酷的现实,一生的遭遇,不允许孔子简单地停留在道德决定吉凶的认识水平上。事实上,道德与否并非总是与结果的吉凶有着必然的联系,这理论常常遭到来自生活的尖锐质疑。以孔子行迹论,抛开政治上的挫折、失意,一生中频遭大难,其最显著者有:流亡其间,与弟子习礼于树下,宋司以桓 欲杀之;过蒲,蒲人止之,弟子公良孺舍死相斗,方免;迁蔡大夫,派人围困孔子于陈,不得行,绝粮,从者病,莫能兴(均见《史记孔子世家》)。最后一次的蔡地绝粮事件,甚至在弟子中造成了信仰危机。尽管当时孔子处变不惊,“讲诵弦歌不衰”,一向质直粗豪的子路仍忍不住有种被命运捉弄的感觉,“愠见(孔子)曰:‘君子亦有穷乎?’”意即,您平素教导我们行仁义定会有好报,现在到了这步田地,该怎么解释呢?另一高足子贡也勃然变色,表示困惑,以至于劝孔子降低追求的标准,以求为世所容。看到群弟子多有不满之色,孔子问子路:“吾道非耶?吾何为于此?”意在探问子路是否动摇了道德信仰。果然,子路的回应似问似答,充满了因惑:“意者事未仁耶?人这不我信也。意者吾未知耶?人之不我行也。”意思是,还是我们道德修养上有缺欠,要不怎么会处于这样不利的境遇呢?似惑实怨。孔子的回答意味深长:“有是乎!由,譬使仁者而必信,安有伯夷、叔齐?使智者有必物,安有王子比干?”指出,遭遇因顿的原因并不在于道德修养的程度不够,以伯夷、叔齐为例,说明仁不必信,以比干为例,说明行不必果。也即是说,仁义之士并不一定“吉,无不利”。
这一观点的提出,等于厢当程度上否定了传统的道德与结果相对应的观念。既然道德未必一定与吉凶结果相对应,接下来的问题就是:吉节从何而来?不能保证必致吉利的仁义道德又有什么价值?前一个问题,孔子在《序卦传》中已经回答了,即《吉凶的出现作为易道的演化有其必然性,并非都是人的意志支配的结果,人需以达观的心态面对这一规律。解决第二个问题首先要撇开道德的功利目的,直接审视其自身的价值。
《说卦传》谓:
昔者圣人之作《易》也,幽赞于神明而生蓍,参天两地而倚数,观变于阴阳而立卦,发挥于刚柔而生爻,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,穷理尽性以至于命。
何为“性”、“命”?《周易程氏传》解为:“天所赋为命,物所受为性”,意即,人作为天地万物之一,其生命的本质——命,是至高无上的易道贴切予的,“性”是“命”落实在个人身上的具体表现。关于“性”与“命”的关系,徐复观先生的分析颇为精彩:
性的根源是命;但性拘即于形体之中,与命脉不能无所限。能尽性,便突破了形体之限隔,而使性体完全呈露;此时之性,即是性所来之命,一而非二,,这就是“至于命”。“至于命”的人生境界,乃是与天地合其德的境界。似神秘而非神秘。
由此我们看到,孔子肯定的人生价值,在于通过仁义道德的实践,实现人性的自我完善,从而体现“命”所具有的易道本质。这一过程是不考虑吉节结果的,是非功利性的。因为,吉节不过是外在于人的自然表现,而“尽性至命”属于“反躬修己”内在修养,君子只需要“正位凝命”即可,并不需要外在的证明。一切都由自己做主,所谓“仁远乎哉,我欲仁斯仁至矣”;一切都以内在的充实为目的,所谓“不怨天,不尤人”、“求仁得仁又何怨焉”。至此,“尽性至命”从理论上解决了类似陈蔡之厄带来的信仰危机。
需要指出的是,“性”、“命”之说的提出,也并非始于孔子。如《左传》成公十三年,刘康公就说过:
吾闻之,民受天地之中以生,所谓命也。是以有动作礼仪威仪之则,以定命也。能为者养之以福,不能者败以取祸。
引文的后两句话,“能为者养之以福,不能者败以取祸”,值得特别注意,它表明,刘康公的“定命”说,需要有福祸结果的功利性支持。孔子与其的根本区别,在于将道德的目的与道德的功利效果剥离开来,使道德实践排除了干扰,具有自身满足的特性。孔子“尽性至命”的理论,在坚守道德立场不变的前提下,回应了来自现实境遇的严峻质问,其立论的深邃、严密远远超过了以往将道德视为吉凶之源的认识水平。长期以来,周人认为,“天”根据人的道德情况来决定人的吉凶祸福,许倬云先生认为这是对殷人认识的突破。
官网:www.yidaofs.cn 版权所有:易道風水網
友情链接

地址:绍兴县会稽山上 绍兴市越城区新建南路861号-绍兴南易文化办事处
联系人:尉汤渺 手机:13757585257 助理:13615758576 邮箱:wtm5257@163.com QQ:929932785 网址:www.yidaofs.cn
版权所有:易道文化网-诸暨市易道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部 浙ICP备10026694号